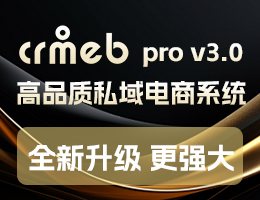如果与狗(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动物)生活在一起,你就会知道它们不仅有你意想不到的聪明,而且会流露出许多情绪。我黑色的德国牧羊犬诺西(Nosy),当它在高高的落基山脉第一次遇到雪时,它将它的鼻子插进这奇怪的白色物中,将它抛洒到空中,并再次接住它。它咬住冰层,对着雪堆叫喊,最后躺在地上来回滑行,将这些冰冷的晶体摩擦到它的皮毛中,这是它对快乐的一种生动展示!当一只小狗加入我们的家庭,当我们的关注都集中到这个新的家庭成员时,诺西好几周闷闷不乐;当它捡回一个乒乓球时,它会兴奋;当另一只狗挑战它时,它会变得好斗;当它犯了一些不准做的错事时,它会羞愧,把尾巴夹在两腿之间;当周围有烟花表演时,它会害怕并需要百忧解(Prozac,一种治疗精神抑郁的药物);当我整天工作并忽略它时,它会无聊;一旦有车进入我家的私人车道,它就警惕起来;在我们做饭期间,当它等待食物撂下来却被某个孩子戳了一下时,它会生气;而当我自杂货店购物返回家时,它会好奇,把鼻子伸进每个袋子去检查里面的东西。
作为群居动物,狗演化出许多各种不同的精细的交流技巧。在动物行为的观察者中,没有人比查尔斯·达尔文更敏锐,更何况他是一个爱狗者,他在《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中就这种犬科的声音这样写道:
同样在追逐时,我们听到渴望的吠声,愤怒的吠声,还有咆哮的吠声;当被关起来时,狗发出绝望的尖叫或嗥叫;夜晚时会嚎叫;当与主人散步时,会快乐地叫;当希望门或窗被打开时,是一种独特的恳求或哀求的吠叫。
狗的尾巴、鼻子、爪子、身体、耳朵和舌头都能表达它的内部状态,即它的感受。狗不会或者它们无法掩饰。
从犬科动物表现出的丰富多样的行为以及其脑与人脑之间无数结构和分子的相似性,我推断狗具有现象感受。任何否定它们具有感知能力的哲学或神学都有严重的缺陷。(当还是孩子时,我就从直觉上感觉到这一点;我不理解在审判日上帝为什么复活人类而不是狗。这完全不可理解。)对狗适用的也同样适用于猴子、老鼠、海豚、鱿鱼,或许也适用于蜜蜂。我们都是自然的孩子,我们都体验生活。
尽管这种论点在西方国家中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因为它们的一神论信仰公开放弃了动物的灵魂,但东方宗教则更宽容些。印度教、佛教、锡克教(Sikhism)和耆那教(Jainism)认为所有生物都是有感知能力的,并且有亲缘关系。美洲原著居民也没有人类例外论的信仰,而人类例外论的信仰在犹太-基督教的世界观中却是根深蒂固的。
事实上,我经常认为狗比人更接近真正的佛性。它们本能地知道什么在生命中是重要的。它们无法忍受恶意或怨恨。它们对活着的喜悦,对快乐的渴求,它们至死也不曾败坏的质朴的忠诚,都是人类只能希求的东西。
数万年前,狗与人类在热带草原、干草原和森林中结下盟约,当时狼与人类开始成为近邻。那种有利的关系——两个物种同时演化,彼此习惯,延续至今。
可是毫无疑问,犬科动物的意识的范围和深度都不及我们。狗不会反思自身或不会为它们的尾巴为什么以一种可笑的方式摇摆而烦心,它们的自我觉知是有限的。它们不会为亚当的诅咒,为自己必死的认识而痛苦。它们不会有人类那样的罪恶,从存在主义的恐惧到大屠杀和自杀式爆炸。
考虑一些更简单的动物(动物的简单性是由神经元的数量及其相互连接来衡量的),例如老鼠、鲱鱼或苍蝇。它们行为的分化程度比狗的更低,它们的行为模式也更刻板。因此,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些动物的意识状态比犬科动物的意识更贫乏,更加缺乏联想和意义。
基于这种推理,学者认为意识是脑的一个涌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y)。生物学家广泛地持有这种观点。涌现属性究竟意味着是什么?涌现属性是由整体表达的,而非必然由其个别的部分表达。系统会拥有一些在其部分中不曾表现出的属性。
对于涌现而言,没有必要诉诸任何神秘的新时代的弦外之音。考虑一下水的湿度,它能够维持水分子与表面的接触,这是分子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是附近水分子之间的氢键的结合。一个或两个水分子不是湿的,但是在适当的温度和压力下,将大量的水分子放在一起,湿性就显现了。遗传法则来自DNA和其他大分子的分子属性。当很多汽车从不同的方向驶向一个过度密集的空间时,交通拥堵就可能出现,你理解这一点。
按照这个刚才定义过的方式,当少量神经元连接在一起时,意识并不会出现;意识出自细胞的巨大网络。神经元聚合越大,对那个神经网络来说可能的意识状态的“数目”就越大。
如果我们要理解意识的物质基础,那么我们就必须深刻地领会:这些紧密啮合的成千上万的异质神经细胞构成的网络是如何编织心智生活这张织锦的。要想形象地表示脑惊人的复杂性,回想那些特殊的自然事物——单螺旋桨飞机在丛林上空飞翔数小时所捕获的亚马逊的浩瀚景象。这个热带雨林中众多的树就像你脑中的神经元(如果森林继续以目前的进度被砍伐,那么这个说法在几年内就不再成真了)。这些树的根、枝和叶被藤蔓和匍匐爬行物覆盖,它们形态的多样性也可与神经细胞相比。想一想那个情景,你的脑就好像整个亚马逊热带雨林。
神经元联合体在与环境以及神经元彼此间的交互作用中,学习能力通常被低估了。单个神经元是异常复杂的信息处理器;(对突触输入进行加工的)每个神经元树突的构型以及(对其输出进行分配的)每个神经元的轴突都是独一无二的。反过来,突触是纳米机器,它的学习算法可以修改这些(时间尺度从几秒到一生不等的)神经元连接的权重和动力模式。人类对于这种巨大、复杂和适应性网络并无多少直接体验。
理解意识如何涌现于脑,这个概念困境在历史上类似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关于活力论和遗传机制的争论。作为遗传基础的化学规律让人极其费解。储存在一个细胞中的所有信息如何说明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这些信息是如何被复制并被传递给这个细胞的后代的?在当时被人们所知的这个简单分子是如何使卵发育成为成人的?
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英格兰遗传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在1916年恰如其分地表述了这个困惑:
生物属性以某些方式附属于一个物质基础,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附属于核染色质;可是难以置信的是,无论多么复杂,染色质或任何其他物质粒子是如何拥有我们的因子或基因必然获得的力量(原文如此)。染色质的粒子(在任何已知的测试中彼此难以区分,而且几乎完全是同质的)通过它们的物质本性赋予事物以生命属性,这个猜想超越了甚至最令人信服的物质主义的范围。
为了解释生命,学者援引了神秘的活力论的力量、亚里士多德的圆满实体(entelechy)、叔本华(Schopenhauer)的现象意志或者柏格森(Bergson)的生命活力。其他学者(例如他们中以薛定谔方程闻名的物理学家欧文·薛定谔())则诉求新的物理学定律。化学家无法想象线状分子中四种类型的核苷酸的确切顺序是理解生命的关键。遗传学家低估了大分子存储巨量信息的能力,他们也不曾理解蛋白质惊人的特异性,这些特异性是经过几十亿年自然选择行动造成的。但是生命这个特殊的困惑最终会被解开。我们现在知道生命是一种涌现现象,并且能最终被还原为化学和物理学。任何活力论的力量或能量都不能将这个无机的死寂世界与有机的生命世界分离开。
缺乏明确的分界线对涌现而言是非常典型的情况。像H2O这样的简单分子显然不是活的,而细菌则是。但是导致疯牛病的朊病毒蛋白质呢?病毒呢?是死的还是活的?
如果意识是一种涌现现象,最终可还原为神经细胞的交互作用,那么一些动物就可能有意识而另一些动物则不可能有意识。微型脑——想想著名的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还没有字母l大,它的脑恰好有302个神经元,可能没有心智。大尺寸的脑(一个人有160亿个神经元)有心智。这种涌现与物理思维的基本训诫——无中不能生有,不一致,这是一个原始守恒律(Ur–conservation law)。如果最初这里什么也没有,那么增加一点不会带来什么差别。
我过去曾是一名意识涌现于复杂神经网络观点的支持者,只要读一下我早期的《意识探秘》(Quest)一书,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但是经过这些年,我的想法改变了。主体性根本不同于任何作为涌现现象的物理事物。蓝色根本不同于眼睛视锥细胞中的放电活动,尽管我完全知道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一个内在于我的脑且无法从外部推断,而另一个具有客观属性,可以被外部观察者获得。这个现象属性来自不同于物理现象的领域,服从不同的规律。我没有看到能够通过更多神经元来弥合无意识生物与有意识生物之间分界的任何方式。
存在涌现和还原论的一个清楚的替代选择,这个选择对像我自己这样隐蔽的柏拉图主义者而言是无法抗拒的。在18世纪早期,莱布尼茨在其单子论中开宗明义地讲道:
1\.我们将在这里讨论的单子(The MONAD)——不过是一个成为复合物一部分的单质——是简单的,即没有组分。
2\.而既然存在复合物,就必然存在单质;因为复合物不过是简单物的一个集合或聚合。
这个观点的确要付出许多人不愿承担的形而上学的代价,即承认体验(功能性脑的内在视角)是根本不同于导致它的物质事物以及体验不曾完全还原为脑的物质属性。
- 推荐序
- 译者序
- 第1章
- 第2章
- 处于科学萌芽期的无忧无虑的童年
- 研究神经细胞的生物物理学
- 加州理工学院、教学、研究和物理学家眼中的脑
- 再次面对意识的冲击
- 第3章
- 感受质和自然世界
- 意识的功能是什么?
- 对意识定义的困难
- 论动物的意识
- 论自我意识
- 第4章
- 在脑中发现意识
- 一览无余的隐藏物体
- 并非所有的神经元都参与意识
- 新皮层的高级区的神经元与意识紧密相关
- 注意到某物,可却没看到它
- 第5章
- 调节意识特定内容的一些灰质小块
- 概念神经元编码了霍默·辛普森(Homer Simpson)和詹妮弗·安妮丝顿(Jennifer Aniston)
- 两个皮层半球中的每一个都能产生意识
- 意识能够永久地消失,留下一具僵尸
- 第6章
- 脑中的僵尸行动者
- 社会无意识
- 无意识无处不在的影响对我的探索意味着什么?
- 第7章
- 自由的强立场与实用立场的细微差别
- 经典物理学与决定论:钟表装置的宇宙
- 钟表装置宇宙的终结
- 心智针对一个量子事件而实现另一个量子事件的自由是有限的
- 作为对行动的事后想法的意志
- 自主性,或这个有意识的意志体验
- 评估这个处境
- 第8章
- 狗,或者意识是出自脑吗
- 意识内在于复杂性
- 意识与信息理论
- 整合信息理论
- 泛心论与德日进
- 一个谦逊的临别想法
- 第9章
- 严重受损患者的意识测量仪
- 运用光遗传学追踪意识的踪迹
- 来到新视域
- 第10章
- 二元论、灵魂和科学
- 宗教、理性和弗朗西斯·克里克
- 自然神论,或作为神圣缔造者的上帝
- 有神论,或作为介入者的上帝
- 启示和经文有帮助吗
- 我曾有过田园牧歌的生活
- 将我的旗帜钉在桅杆上
- 注释
- 第1章
- 第2章
- 第3章
- 第4章
- 第5章
- 第6章
- 第7章
- 第8章
- 第9章
- 第10章
- 译后记